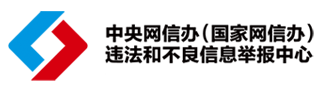来源:中国教育报
作者:黄亚婷 潘仁同
时间:2025-03-27 10:01:26
没有组织的科学是没有力量的。1931年,“计划科学”的概念在苏联被首次提出,并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扩散至全球,此后,“大科学体制”逐渐成为一些国家实施重大科学工程的重要举措。如今,以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为导向的有组织科研模式,仍然是全球主要国家加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瓶颈、提升全球科技竞争力的战略性制度安排。作为基础研究主力军和重大科技创新策源地,研究型大学是开展高水平有组织科研的主要力量。美国、法国、瑞士、英国和澳大利亚等国家的研究型大学,从理念引领、治理架构、跨界链接和评价变革等方面系统推进有组织科研。
国家战略需求激发有组织科研动力
有组织科研作为一种建制化的科技创新范式,是在国家战略需求牵引和经济社会发展驱动的双重作用下,通过整合政府、高校、企业和科研人员等创新主体,构建起来的协同创新体系。这一体系既体现了国家意志对科技发展的战略导向,也反映了科技创新深度融入国家发展全局的时代特征。
法国研究型大学注重围绕国家战略需求、国家和社会面临的主要现实问题开展有组织科研。法国大学的有组织科研从研究院、高校和国家三个层面加以系统实施。如巴黎政治大学的社会不平等问题研究中心,顺应社会发展需要,经历了从社会结构变迁向社会不平等问题研究的战略转向。在具体实施层面,巴黎政治大学负责引进人才和调配资源,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负责提供制度化、长效化的顶层设计支持。
在瑞士,以服务国家战略需求为牵引,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结合学校科研优势和发展基础,确立了数据科学和人工智能、健康和医药、材料和制造、可持续发展等有组织科研重点领域,建立了针对战略重点急需领域进行科研攻关的研究中心,通过构建国内外创新网络,开展对瑞士科学、经济和社会发展有战略意义的科学研究。
美国则注重探索以有组织科研提升国家整体创新效能。一方面,在科技创新和技术突破的战略布局中,美国国家实验室在物理、化学、生物、材料科学和信息科学等关键领域进行系统性部署。另一方面,分布在各所大学的实验室对接国家需求,在核能技术、人工智能、微电子等关键领域持续发力,深度参与了费米伽马射线太空望远镜、普朗克宇宙微波背景辐射探测等科学工程。
治理结构转型保障有组织科研运行
研究型大学有组织科研的特征是内部治理的高度“组织化”。遵循大科学研究规律,研究型大学较多采用主任负责制的权力分配模式和扁平的组织管理模式。
美国研究型大学采用主任负责制,实验室主任被赋予双重权力,既掌握学术资源配置、规则制定等学术决策权,又负责人事聘用、薪酬设定等行政事务。这种制度设计有效减少了外部干预,增强了实验室的自主治理能力,使其能够较快响应科研需求的变化,以保持持续创新的能力。
瑞士研究型大学采用灵活的组织结构,成立国家级和校级研究中心,以研究小组为单位建立结构化体系,创建跨学科联合实验室,聚集不同领域研究人员,整合战略目标并开展科研工作。
法国研究型大学则将扁平化组织结构进一步拓展为平行贯通的学科交叉制度。如巴黎政治大学在协调学科—科研—教学的关系方面进行制度创新,以平行贯通制度实现科研组织与教学组织的分离,从而将科研工作从繁重的教学任务中解放出来,以此强化科研组织的研究型定位。
跨界合作网络推动有组织科研协同
重大前沿问题攻关,并非一个学科、一个团队或是一所高校能够单独胜任的,研究型大学有组织科研的意义正在于此——通过打破学科壁垒和组织壁垒,以有组织的形式系统建构跨学科、跨领域、跨行业的无边界合作网络,从而为复杂现实问题的解决提供创新方案。
瑞士研究型大学将学科交叉培育项目作为跨界合作的核心载体,推动自上而下的国家战略与自下而上的跨学科实践深度融合。例如,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发出学科交叉研究倡议,密切加强与洛桑联邦理工学院、苏黎世大学等学校和机构的合作,聚焦数据科学、健康和先进制造领域,打造广泛且紧密联系的跨学科合作网络。
法国研究型大学则形成了独特的校内外合作机制——在校内构建跨学科机构,实现内部紧密合作;在校外完善多学科合作网络,畅通外部合作渠道。如巴黎政治大学校内的3个基于交叉学科组织的科研机构,不仅推动校内的跨学科合作,还分别与其他大学的不同机构建立联系,呈现出网状分布式合作特征,有助于减少学科壁垒对不同机构间合作意愿的抑制效应,以实现从单一学科向多学科领域的拓展。
美国研究型大学则力图构建连接国家实验室、学界、产业界等的跨界合作网络,通过形成跨越“实验室—企业”边界的科研成果转化区域、跨越“实验室—社会”边界的公共服务区域、跨越“实验室—学界”边界的科研合作区域等,构建多元跨界生态,并以产业链与创业链的双向融合实现跨界生态的利益共享。如麻省理工学院要求其管理的林肯实验室与企业、研究机构等实体组织一同加入“战略合作伙伴项目”并签订战略协议,在实现多学科、多部门跨界联合的基础上,规范、引领资源共享过程,促进主体间形成知识生产和科技成果转化的创新联合体,深度推进产业链与创新链的融通和共生。
科研评价变革助力有组织科研创新
有组织科研是科研模式的系统性创新,而科研评价机制变革是推动有组织科研从模式创新转向成果创新的关键环节。受制于有组织科研任务难度系数大、内容复杂等特性,研究型大学有组织科研的评价机制迫切需要从绩效导向的量化评价转向质量导向的创新贡献型评价。
为此,美国研究型大学设置了跨学科研究成果评定与职称晋升联动的评价机制,以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评价体系,实现对研究者创新成果、实践能力和在跨学科合作团队中贡献的综合性评价。值得关注的是,部分研究型大学将国家实验室的跨学科成果纳入科研人员个人年度绩效评估考核范围,并给予跨学科团队每位成员与独立作者相同的绩效积分,力图避免因竞争导致组织资源损耗和创新效率降低。
英国研究型大学系统变革了科研资助评价体系,从科研文化建设、社会影响力提升和成效监测三个方面提升科研资助评价体系的科学性。英国医学研究理事会是英国生物医学研究领域的主要科研资助机构之一,它研制了“科研文化成熟度评价模型”,以激励科研组织构建有助于战略科技人才成长发展的良好文化。同时,为保证科研组织重视成果质量而非数量,英国医学研究理事会参与开发了结构化的“科研团队社会影响力叙述性模板”,要求科研团队在项目申请过程中提供完善且翔实的描述而非简单的论文发表数量,并施行立项资助后的成效监测和数据公开机制,助力有组织科研的持续改进。
澳大利亚研究型大学建构了“澳大利亚卓越科研评估”与“社会互动和影响力评价”两大评价机制。前者侧重采用量化的方式评估科研成果的学术质量,后者侧重采用质化评估的方式评估高校科研人员的社会互动程度和科研成果转化等表现。澳大利亚采用这种质化与量化相结合的评估机制,试图推动研究型大学有组织科研的创新性发展。
(作者单位系浙江大学教育学院,黄亚婷系该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本文系全国教育科学“十四五”规划2023年度国家一般项目“我国研究型大学有组织科研的实践机制研究”[B1A230174]成果)